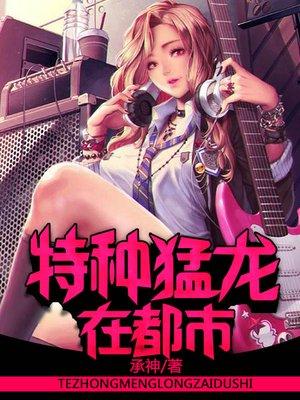叶凡小说>江湖小神捕 > 第二章 城中怪客(第1页)
第二章 城中怪客(第1页)
一场春风春雨之后,天晴日暖,南来北往的行人也多了起来。
人多了难免有争执。
寻常人若起争执不过掀桌子砸碗,或者互相给个三拳两脚。要命的是那些略懂些武功的江湖人,稍有冲撞便要动刀动枪,轻则伤筋断骨,重则要人性命。一时的激愤过后,也有也觉得下手太重的,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,轻易难以化解,于是结仇、结怨、结恨。仇恨怨念蔓延,新仇旧恨叠加,终于成了血仇不死不休,而后终日寻仇觅恨,不得消停。
这几日,来往潞城的江湖人突然多了起来,潞城衙门一时之间查不出缘由,只得多多增加巡街的捕快,无论如何总能减少些争执,也避免闲杂人等趁机生事。
天刚过正午,正是客栈里最忙的时候,小二刚刚在大堂内收拾完饭菜,便听见门外迎客的小厮高唱道,“打尖的四位,里边请来!”
随后便见四个客人走了进来。
那四人都是四十岁上下,眉细眼小,嘴边留着两撇老鼠须子,头发都是乱糟糟地扎起来,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松松垮垮,但身上却各有一个和本身松垮乱糟的几人及不相称的东西。
走在最前面的一个带着绣雄鹰的皂角巾,后一个披着绣猛虎的文武衣,再后一个系着个绣飞熊的腰带,最后那个穿着绣着豹子黑靴。这几件都是金丝绣成,上镶嵌着多色宝石,外面套着个鹿皮银狐领的短袍子,很
是惹眼。
四人抬着个大红木箱子,进门寻个空位,正准备落座,突听扑通一声,木箱子重重地落下来。
带着皂角巾的,先是吓了一跳,随即怪叫道,“老三老四,你们两个混球,咱们性命全指望着它呢。”说着突然发现其余三人齐刷刷地看着他,又嘿嘿一笑,“哦对,孟姑娘说了,不能说混球。”说罢一瘸一拐地绕着木箱转了一圈,见木箱无损,正要坐下,又见木箱挡着去路。
那神情木讷的一个随意将木箱踢开,道,“结实,无碍。”
正巧,此时一个小孩正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檀木雕花的匣子进来。看他样子不过八九岁,身形黑瘦,头发散乱地从童子帽下露出来,一双眼睛又黑又亮。
好巧不巧,这小童被突然踢过来的木箱绊了一跤。就听扑通一声,一个瓷器从锦绣匣子中滚落,摔得个粉碎。
小孩瞬间红了眼眶,蹲在地上号啕起来,“哎呀!这可是我们家员外的宝贝,我这该怎么跟交代!”
那四人全都无动于衷,只上下打量这小孩和满地的瓷器,然后却不理会,仿佛和他们没有关系。
周围人都看那小孩可怜,又看那一地泛着天青色的碎片,无不惋惜。
有的道,“你们几个,弄坏人家小孩的东西了!”
有的道,“哎呀,看着可是上好的瓷器啊,可惜了!”
有的惋惜道,“看着有些年头,能值不少钱吧!”
有的恨恨的道,“
要我说得报官,不能这么赔钱了事。”
有的却又像是劝解,“我看这几位仁兄也不是有意的,赔了钱就算了,是不是?”
那四人见众人群情激愤地围着他们,奇怪道,“这是说我们呢?”
一个道,“看样子是。”
那爱笑的一个转头奇怪道,“赔什么钱?谁赔谁?”
一个道,“箱子绊倒的他们不找箱子赔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