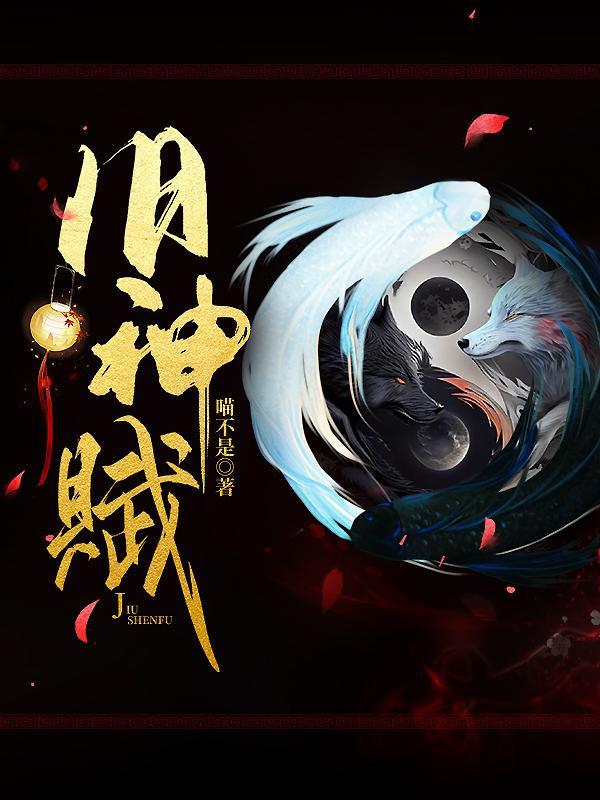叶凡小说>恶灵诅咒:第一位温迪戈 > 第101章 饿殍(第1页)
第101章 饿殍(第1页)
阿斯兰王庭的皇宫之外,繁华如同过渡一般,随着距离的渐远,奢靡的质感直线下滑。
除却中心区,以及几条所谓的“贵族区”,其他地方几乎与贫民区无异。
其中的人们饥饿又无力,在那些狭窄阴湿的巷道或是角落里徘徊,寻找希望,或是倒在寻找希望的路上。
他们幻想着先贤的到来,但想象的形象是圣教所篡改的模样。
然而,每当有人提出维多利亚的恶劣,咒骂阿尔比昂的苦难无从救赎的时候,这些人大多都会热血上头,似乎这片国度给了他们什么重要的东西似的,如狂信徒一般去攻击那个抗议者。
提到维多利亚的工业远超大地诸国的时候,就算是将要饿死的乞丐也会挺起自己的脊梁。
悲哀,愚不可及。
当无数装甲部队浩浩荡荡从各个大道涌向皇宫集结,这些愚昧的人们纷纷将注意投向了这边。
“好多士兵……难不成是要战争了吗?”
此人的表情忧心忡忡,摸了摸自己的肚子,干瘪的肚皮下几乎要枯萎了一般。然而旁边的贫民却一脸兴奋。
“战争?太好了!壮哉我阿尔比昂,维多利亚武德昌盛!”
他高呼着,就仿佛战争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。
于是,又一人发话:
“你高兴什么?战争来了,我们就是最先被抛下的!”
“你什么意思?”
被驳斥的那人转头揪着对方的衣领,这张面孔上看不见丝毫理性,唯有一种疯癫的狂热。
“你是在否定阿尔比昂的伟大吗!该死的叛国贼!”
咬牙切齿,形同恶鬼。
其他人或多或少带着怜悯看向这个大吼大叫的家伙,又可恨这种人偏偏就在眼前风言风语。
多少人的先辈为阿斯兰卖命,结果呢?沦落到贫穷的境地,到他们这一代,所谓的“胜利的果实将有战士们分享”的恩泽是压根屁都没有,阿斯兰改名维多利亚之后就仿佛是丢掉了虚伪的面纱,全然不再理会这些底层的未来究竟如何。
他们至少还在维多利亚的不列颠城,冬天在暖气管附近还能勉强借用那些老爷的室外管道取暖,那其他地方呢?
多半是比他们现状的模样还要凄惨。
然而就算这样,还是有此类迷了双眼的混账,拥戴这个一毛不拔的吝啬国度。
很多人想过去别的地方——卢萨亚、大煌、埃佩格……哪里都好,只要能有条活路。
可是放眼看去,好像哪里都有着近似的压迫滋生不幸,从未有一个安稳的地界能够容纳一份干净的和平。
人们看似接受了现实,实际上更多的是对于无奈的放手。
肉体的挣扎已然无济于事,那么仅剩的,便只有精神上的抵触。
可偏偏有的人把这种沉默的抵触当成是默认的忠诚——
“你这家伙,”这个估摸着已经没多少理智的男人扯着眼前的人,双目圆瞪,“你这不忠诚维多利亚的反贼,我要替阿斯兰的荣光制裁你!”
肮脏的拳头举起,当即要砸向对方的面门。
其他人赶忙拉住,也许是这个疯子的极端引爆了大家的压抑,一股无名火开始从众人的心头膨胀。
“他妈的蠢货,给我清醒点!”
这人挨了一拳,但也因为这一拳,整个人燥热起来,在肾上腺素的激发下,整个人的皮肤都有些泛红。
他猛然挣脱左右的拉扯,上去就是一巴掌,重重轰在出拳者的太阳穴。
被打的人只觉得耳朵突然一闷,接着听见一声什么破了,便听不见任何东西。
“来啊,你们这些阿尔比昂的叛徒!等我把你们都杀掉,阿斯兰王庭一定会封我当护王骑士,我的忠诚一定会被看见!”
这个极端的男人又扑向刚才那个驳斥他的家伙,全身的力气大得出奇,每一下出拳都带着血花飞溅,而那副因为狂喜而咧开的表情就跟个魔鬼似的,旁人都觉得胆寒。
而他口吐狂言的内容,究竟是真的如此相信,还是疯掉之后的妄言,已经不为而知了。
这场血腥的斗殴过了很久,受伤的人很多,毕竟大家连吃饱饭痊愈都难,加上贫民享受不到足够的医疗,说不定得留下些后遗症,更严重的说不定会害上重病,熬不过这个冬天。
直到一声令众人心头一颤的践踏声从大道那一头传来,事情才算有所收尾。
轰——